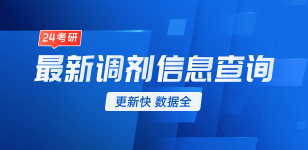徐飛
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迅猛發展正在重塑全球教育格局,商科教育首當其沖面臨知識體系迭代、人才培養模式轉型的雙重挑戰。基于AGI時代的技術特征與教育變革邏輯,AGI的“可編碼能力”優勢,倒逼人類向“非編碼能力”遷移,而直覺思維、倫理判斷、創新設計等非編碼能力,構成了未來商科人才的核心競爭力。
一、AGI時代的教育革命與商科教育的現實挑戰
(一)AGI“元革命”
AGI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通用核心技術,正在引發人類社會的“元革命”。之所以稱之為元革命,是因為歷次工業革命/技術突破只是人類智能(Human Intelligence:HI)的產物,都無關HI,唯獨AGI是關乎智能本身的革命,是完全以接近甚至超越HI為目標的技術。與傳統專用人工智能(ANI)不同,通用人工智能(AGI)具備跨領域問題解決能力,其底層技術架構(如Transformer模型)不僅實現了知識的高效檢索與重組,更催生出“智能體(Agent)”這一具備自主學習、任務執行與工具使用能力的新型系統。概言之,AGI的本質上是“工具的革命”向“革命的工具”躍遷,其對教育的沖擊遠超以往任何技術形態。實際上,當AI能夠在納秒級完成人類知識庫的檢索與重構時,以知識積累為核心的教育范式已難以適應時代需求。
(二)第四代大學呼之欲出
世界大學發展的歷程,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和1200年法國巴黎大學的誕生,標志著第一代(中世紀)大學出現,其核心是知識傳授。1810年威廉·馮·洪堡創辦柏林大學,開啟第二代(近代大學)時代,大學在傳授知識基礎上重視知識創造,形成“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統一”的理念,并確立了“教學與科研并重”的原則。1904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查爾斯·范·海斯校長提出,大學應具備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三大職能,現代大學(第三代大學)至此成型。進入21世紀,隨著AGI技術的迅猛發展,大學教育迎來了新的變革契機,第四代大學呼之欲出。以可汗學院、奇點大學、密涅瓦大學等為代表的新型大學,以及以高舉“開環大學(Open Loop University)”旗幟的斯坦福大學為代表的諸多銳意改革大學,展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質,其最鮮明的特征是大學與AI深度融合。以密涅瓦大學、奇點大學為例,其課程設計不再局限于學科邊界,而是以解決氣候變化、數字治理等復雜問題為導向,強調AI工具與人類創造力的協同。這種轉型在商科領域尤為迫切——傳統商學院賴以生存的“知識傳授”職能正被智能教學系統、數字人導師等AI應用逐步替代,迫使教育者重新思考“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
(三)商科教育的現實挑戰
AGI的沖擊在商科教育領域具象化為六大現實挑戰。
一是知識半衰期驟降。工業時代知識更新周期約20-30年,信息時代縮短至5-6年,而AGI時代已逼近1年乃至更少。為數眾多的商學院畢業生因所學知識被AI快速迭代,而面臨“走出校門即知識過時,畢業即失業”的窘境,即便像哈佛商學院這樣的全球頂流商學院,調研顯示63%的畢業生認為,其所學知識在入職三年內已部分過時。
二是AI智能體的“黑洞效應”顯著。基于數據閉環的AI系統,呈現“越智能越易獲取數據,越獲取數據越智能”的“數據-智能”正反饋機制,導致人類在“可編碼知識”領域的劣勢持續擴大。劍橋大學研究發現,AI在標準化考試中的得分年均提升15%,而人類同期僅提升2%。
三是高校專業結構深度調整。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數據顯示,2020-2024年美國商科本科招生量下降12%,而計算機科學專業增長27%。類似地,中國現有的14大學科門類中,理工農醫類因技術剛需持續升溫,而文史哲經管法教藝等文科專業招生遇冷。尤其是原來量大面廣的商學院生源持續萎縮,不少學校MBA和EMBA的報考人數小于招生計劃數,有的高校甚至停招商科本科生。
四是勞動力市場重構。AI不僅替代低端體力勞動,更向財務分析、市場調研等腦力崗位滲透。德勤研究表明,2024年全球30%的財務報告由AI生成,傳統財務崗位需求年均下降8%。
五是商學教育供給端和需求側結構性失衡。發展新質生產力和進一步深化改革,對復合型經管人才和相關研究的巨大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落差。
六是對商學教育價值質疑,這也是所有挑戰中最根本、最深刻的。商科培養的人才沒有展現出令人信服的變革領導力;實踐能力和創新思維培養不足,創新創業教育、針對中小企業管理的教育關注不足等也常被詬病。
二、非編碼能力
(一)可編碼與非編碼能力的二元分野
AGI的替代邏輯遵循“可編碼性”原則:凡是能夠通過數理模型量化、具備標準化流程、存在明確答案的任務(如會計核算、軟件測試、語音生成),均可能被AI高效替代;反之,那些依賴情境判斷、充滿不確定性、需要價值權衡的“高灰度“任務(如戰略決策、心理咨詢、跨文化談判),則構成人類的“能力護城河”。這種分野可通過2023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AI智商淹沒曲線”直觀呈現:在任務結構化程度坐標軸上,圍棋(完全結構化)、翻譯(半結構化)、創業決策(非結構化)形成連續譜,AI表現隨結構化程度升高呈指數級上升,而人類優勢集中在非結構化區間。MIT的腦科學研究表明,人類前額葉皮層與默認模式網絡的連接強度,與非編碼能力呈正相關,這為能力培養提供了神經科學依據。
(二)非編碼能力的核心維度
21世紀商業思潮的拓荒者、著名未來學家趨勢專家丹尼爾·平克,在《全新思維》中提出決勝未來的六大能力:設計力、娛樂力、意義力、故事力、交響力和共情力。顯然,這六種能力都屬于非編碼能力。實際上,非編碼能力并非單一維度的技能,而是融合靈性、認知、情感、倫理的復雜體系和立體架構,其核心構成包括:
1.直覺與靈性認知。在人類認知的廣闊領域中,潛意識洞察、第六感官、頓悟能力等“非邏輯認知”,當屬獨特而神秘的非編碼能力。這些能力突破常規邏輯框架,以超越理性分析的方式,捕捉事物本質與潛在關聯。研究表明,90%的創新機會源于直覺思維,它如同黑暗中的明燈,指引著突破與發現。榮格心理學深刻揭示,直覺是連接個體意識與集體無意識的橋梁,集體無意識中蘊藏著人類長期進化積累的智慧,直覺讓我們得以從中汲取靈感。這種能力并非遙不可及,而是可通過系統訓練強化。哈佛商學院的實驗頗具說服力,8周正念訓練后,學生在商業洞察測試中的準確率顯著提升23% 。通過冥想、深度內省等方式能喚醒內在直覺,解鎖認知新維度,我們在復雜世界中能獲得獨特的理解與洞見。
2.倫理與情感智慧。AI無“ai”(愛),AI不僅不具備良知判斷、責任擔當、共情能力、團隊領導力等“軟技能”,更無法理解人類情感需求。其實,商業活動的本質是“人的連接”,倫理缺失可能導致技術濫用(如算法歧視、數據壟斷)。沃頓商學院開發的“道德判斷測試”(MJT)顯示,通過腦電波分析(如P300成分)可有效預測管理者道德行為一致性,其相關系數高達0.68。
須知,當技術浪潮沖刷掉知識的“沙灘城堡”,留存下來的必定是人類文明的精神根系——對真善美的追求、對他人的共情、對未知的好奇心,以及在不確定性中堅守價值的能力。AGI恰如孫悟空能力超強,但商科教育的使命,卻在于培養能夠駕馭技術浪潮的“數字唐僧”——未必精通代碼,但一定擁有明確的方向感、強大的心力與溫暖的人性光輝。未來的商業領袖,將是“AI智商”與“人類情商”的平衡者,在技術理性與人文關懷的張力中,開辟可持續發展的新賽道。
3.創新與批判性思維。在AGI時代創新與批判性思維愈發關鍵。好奇心驅動的問題重構能力,能夠打破常規認知邊界,以全新視角重新定義問題本質;跨領域聯想能力,則如同搭建思維橋梁,將不同學科、行業的知識與經驗融會貫通,激發創意火花;而對既有范式的質疑精神,更是創新的基石,敢于挑戰傳統框架,突破思維定式。這三大能力相輔相成,共同構建起強大的非編碼思維體系,助力個人與組織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實現突破與發展。
4.能量智能與流體智能。一般地,可將人類智能解構為“能量智能”+“物質智能”,其中,能量智能是系統或個體高效管理和利用能量的能力,涉及能量的獲取、存儲、轉換和使用;物質智能則是系統或個體有效管理和利用物質資源的能力,涉及物質的獲取、存儲、轉換和使用。人類智能亦可解構為“流體智能”+“晶體智能”,其中,流體智能涉及新問題和自適應推理,通常解決所見問題能力良好,但難以進行新穎的推理;晶體智能則涉及先前知識及其應用,通常知識保留能力強,但公開數據有限。在這四種智能中,物質智能和晶體智能可被AI模擬,能量智能和流體智能則是人類所獨有。后者突出表征的精神和“心力”——包括自驅力、使命感、抗挫折能力等,如同“唐僧”之于“孫悟空”,決定著技術應用的方向與邊界。
(三)人機對齊困境
AGI的工具屬性使其呈現“渣男”特性: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它不會主動發起有益人類的行動,只會被動執行指令,且對結果不承擔倫理責任。例如,算法推薦系統可能加劇信息繭房,但AI本身無需為此負責。亞馬遜AI招聘系統曾因數據偏見降低女性簡歷評分,暴露技術中立性神話。需知,當下強調的“人機對齊”(Human-AI Alignment),核心是“技術向善”,因此,商科教育的一大關鍵命題是培養學生駕馭技術的能力,而非被技術操控。這要求教育者引導學生思考“我們需要怎樣的AI?如何用人類的價值觀馴化技術?”。實踐中,歐盟《人工智能法案》(2023)嘗試建立“分級責任制度”,要求商科教育提前培養學生“算法審計”能力,如使用Python工具包檢測訓練數據偏差。
三、非編碼能力培養的理論框架與實踐路徑
(一)能力培養的雙維模型
基于認知科學與教育理論,可構建非編碼能力培養的雙維模型:能量智能×流體智能。
在橫向維度激活能量智能。通過哲學思辨、倫理研討、領導力實踐等課程,喚醒學生的使命感與價值觀。例如,開設“商業倫理與AI治理”課程,引導學生討論自動駕駛的道德困境、數據隱私保護等議題,強化“技術向善”的理念。
在縱向維度提升流體智能。設計“問題驅動型”學習場景,通過案例分析、沙盤模擬、跨界項目等方式,培養學生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如借鑒密涅瓦大學的“全球沉浸計劃”,讓學生在真實商業場景中解決復雜問題,提升自適應推理能力。
(二)教學范式的三大轉型
1.從知識搬運到認知引導,教師角色轉向“元認知”引導者。一般地,知識可分為事實性知識、概念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元認知”知識。其中,元認知就是對認知的認知,也就是關于個人自己認知過程的知識,調節這些過程的能力,對思維和學習活動的知識和控制。元認知是可以橫跨學科的真正可遷徙的知識,包括戰略方面的知識,關于認知任務的知識(即情境、條件),以及關于自我的知識。
例如,在戰略管理課程中,教師不再單純講授SWOT模型,而是引導學生思考:何時該用SWOT?其假設前提是什么?在AI時代如何迭代該模型?同時,借助AI學術助手(如GPT-4)完成文獻綜述、數據處理等基礎工作,教師聚焦于培養學生的問題定義能力與批判性思維。教師還可使用ClassMarker等AI工具對學生討論進行語義分析,實時生成“批判性思維熱力圖”,自動推送引導問題。
2.從標準化教學到場景化學習,構建“真實場景+虛擬仿真+AI輔助” 的混合式學習生態。其中,真實場景通過與企業合作開展“沉浸式項目”,如為初創企業設計商業模式,在實踐中培養方案落地能力;虛擬仿真利用數字孿生技術構建商業模擬環境,讓學生在虛擬市場中體驗戰略決策的復雜性;AI輔助通過智能教學系統實時分析學生的思維路徑,生成個性化反饋報告,如指出“該決策忽略了跨文化因素,建議參考XX理論”。典型的例子有,斯坦福大學“虛擬企業挑戰賽”利用Unity引擎構建元宇宙商業環境,學生向具情感計算能力的AI客戶推銷產品,系統根據微表情評估共情能力。清華大學“非編碼能力數字孿生系統”通過智能手環采集HRV數據,評估壓力應對能力。
3.從單一評價到能力圖譜。傳統以考試為中心的評價體系難以衡量非編碼能力,需引入多元化評估工具。過程性評估通過課堂辯論、項目提案、團隊協作表現等,評估學生的溝通能力、領導力;倫理決策測試通過設計兩難情境(如“是否為短期利益犧牲用戶隱私”或“是否披露環保違規”),考察學生的價值觀;AI能力畫像利用學習分析技術(LAT)追蹤學生的認知發展軌跡,生成包含“問題提出能力、人際鏈接能力”等維度的動態能力圖譜。
(三)構建“非編碼能力矩陣”,重構課程體系
商科課程需打破學科壁壘,圍繞非編碼能力的核心維度重組內容。在基礎層,開設“直覺與創新思維”“商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等必修課,討論自動駕駛道德困境等議題,奠定認知與倫理基礎;在應用層,設置“跨文化管理與共情力”“人機協同設計”“復雜系統決策”等模塊,培養實踐能力;在拓展層,引入“藝術與商業創新”“哲學與領導力”等跨界課程,激發想象力與跨界整合能力(交響力)。例如,南洋理工大學“能力積分制”允許學生通過AI倫理辯論獲取學分,通過這一舉措畢業生創業率三年提升27%。福耀科技大學擬試點“AI+商業”課程,學生需運用GPT-4生成市場調研報告,再通過小組辯論評估報告的倫理風險與戰略價值,實現“技術應用”與“價值判斷”的融合。
四、構建人機共生的商科教育新生態
(一)教育者的自我革新
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60%標準化教學任務將由智能體承擔,教師知識傳遞職能的不可替代性年均下降15%。鑒于此,AGI時代的教師亟待提升三重能力。(1)數智力:熟練運用AI大模型(自然語言大模型、推理大模型、多模態大模型)及AI工具輔助教學,如使用ChatGPT設計討論題、用Tableau可視化學生學習數據;(2)認知教練能力:引導學生理解AI的優勢與局限,培養“批判性技術觀”;(3)生態整合能力:協同企業、政府、技術平臺等多方主體,構建“教育-產業-研究”的閉環生態。例如,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倫理決策模擬系統”,將前沿技術轉化為教學資源。
(二)學生需完成從“知識消費者”到“價值共創者” 的角色轉變
商科學生需完成從知識“被動接受”到“主動創造”的轉型,為此需在三方面發力。一是成為AI的“馴養者”,學會向AI提出高質量問題(如“如何用第一性原理重構這個商業模式?”),而非依賴現成答案;二是構建“T型能力結構”,即垂直領域知識(晶體智能)+跨領域整合能力(流體智能)。摩根大通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項目中,學生發現的算法歧視問題使少數族裔貸款通過率提升18%,體現“AI馴養者”價值;三是積極參與技術倫理建設,通過實習、競賽等渠道,為企業的AI應用提供人文視角的建議,如設計“包容性算法”減少偏見。
(三)教育政策與制度創新
政府與高校需共同推動系列改革。比如,學分制改革。可借鑒新加坡模式,允許學生通過參與AI倫理研討、社會創新項目等獲取學分,打破“課時-學分”的剛性關聯;進一步完善校企合作機制,建立行業級“倫理沙盒”,如金融領域算法公平性測試平臺。可要求企業為學生提供“人機協同實踐崗位”,如“AI產品倫理顧問”“智能決策分析師”,將職場場景轉化為學習場景。同時,啟動師資培訓計劃,設立“AGI時代教學創新基金”,支持教師開發非編碼能力培養的新課程新工具。亦可設立“人機協同教學導師”認證,對接德國雙元制經驗。
結語。AGI的崛起并非人類能力的終點,而是進化的新起點。AGI時代的商科教育,不是與AI比誰記得更快,而是要回答“我們究竟想成為怎樣的人”。這或許就是非編碼能力的終極意義——在數字荒原上培育出精神根系,在算法統治的世界里守護人類獨有的溫度與光芒。
作者簡介:
徐飛 博士,文科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美國哈佛大學、MIT高級訪問學者,出版著作20余部。歷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西南交通大學校長,現任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
① 凡本站注明“稿件來源:教育在線”的所有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稿件,版權均屬本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本網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經本站協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時必須注明“稿件來源:教育在線”,違者本站將依法追究責任。
② 本站注明稿件來源為其他媒體的文/圖等稿件均為轉載稿,本站轉載出于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轉載稿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在兩周內速來電或來函聯系。






 教育在線
教育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