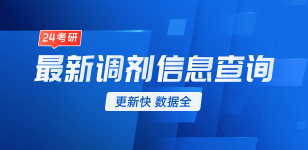一、問題的提出
歷史悠久的大學往往擁有辦學傳統、校友支持,社會口碑等方面的優勢積淀。人類的進化、社會的演化都影響著大學的發展進程,刺激著一輪又一輪新大學的產生。盡管新大學繼承著大學的基因,但每一輪“新大學運動”的出現及其發展都推動著大學的組織變革和發展模式新生。本研究借用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司官網公布的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數據,研究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建在多國的年輕研究型大學是否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發展狀況及其模式。
21世紀已走過第一個25年。在已有“985工程”“211工程”“雙一流”建設高校等“大學群”的中國,一小批“新興的”或稱為“新型的”研究型大學蓬勃興起,較早建立的南方科技大學于2010年12月籌建、2012年4月“去籌”;上海科技大學于2012年4月籌建、2013年9月“去籌”;西湖大學在2018年2月得到設立批文。由于這幾所新建的研究型大學的快速發展,也基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急切需要,教育部批復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步伐加快:2024年5月建立康復大學(青島)和深圳理工大學;2025年2月建立福建福耀科技大學;2025年6月建立大灣區大學(東莞)和寧波東方理工大學。
這種年輕研究型大學得以快速發展的案例僅出現在中國嗎?其他國家是否也有類似情況?如果是,建在不同國家的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狀況和趨勢會有相似性嗎?建校時間甚至發展速度都相近的大學是否有著相同或至少相近的發展模式呢?
結合如上問題,本研究剖析了多國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狀況,用數量研究和比較分析的方法,歸納得出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模式及其特征。為了研究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生命歷程,把對中國21世紀建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研究擴展到對具有不長于50年歷史的年輕研究型大學群體的研究中。
二、研究總體設計
(一)可供研究的條件
本研究獲取研究對象的初始方式是網絡查詢并不存在的“世界大學名錄”,期待得到各國建校時間不長于50年且快速發展的大學。由于國家數量多、語言種類多以及對“快速發展”的非共識,初始努力難以達到研究目標。經查資料得知,擁有“世界年輕大學”數據庫的有THE(Times Higher Education)和QS(Quacquarelli Symonds)兩家公司。為確定數據來源,需要對本研究的數據需求與數據庫資源進行匹配度分析。一是比較數據的豐富度:QS安排50所未滿50歲的大學上榜(Top50 Under 50),THE安排的是不大于50歲的100所大學上榜(TOP100),后者的數據資源相對比較豐富;二是比較所用分析維度與作者研究思想的契合度:QS用聲譽調查、論文引用、國際化、師生比、畢業生就業和可持續發展來判斷大學發展,THE則大致基于大學職能來判斷大學發展,后者的分析維度比較符合筆者持有的基于職能履行的視角。因此,選擇THE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數據庫作為本研究的基礎參考。
(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概念
“年輕研究型大學”實際上就是建校時間不長的研究型大學。研究型大學,最早追溯到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將研究引入大學”和“大學舉辦習明納(Seminar)”興起于德國的大學,1810年建立的洪堡大學對大學科研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推進。1900年美國大學協會的成立,由于其對會員大學的要求和協會的聯盟性質,被稱作“研究型大學”的松散性組織,盡管當時并沒有出現“研究型大學”字樣。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所做的“高等教育機構分類”(以下簡稱“卡內基分類”)及其帶來的多國響應,才使“研究型大學”開始成為多國高等學校體系中的一個類型。由于該分類指標的嚴格限定,“研究型大學”處在多國高等教育機構體系的“頂層”。
研究型大學的概念具有歷史縱向的發展與地域橫向的“漂移”。羅杰·蓋格(Roger Geiger)認為,美國大學協會提出的入會標準是必須進行“高等學習、研究生教育和通過研究促進知識的增長”,即進行大學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科學研究。筆者將卡內基分類中有關研究型大學的入選指標概括為“三多”:本科生教育學科數量多,研究生教育中博士學位授予數量多,聯邦政府支持的科研經費多。在美國研究型大學成就的影響下,英國“研究主導型大學”(Research-Dominated Universities)、澳大利亞“研究密集型大學”(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ies)、中國和日本的“研究型大學”也都現身在世界高等教育舞臺上。結合縱向與橫向研究,筆者曾在2010年給研究型大學以概念上的“四個強調”:強調博士生的培養能力(數量與質量),強調科研的層次水平與經費額度,強調教授的同行認可度,強調可使上述博士生、教授、科學研究在多學科和學術自由中共同發展的大學環境。
THE“世界年輕大學排名”說明,“年輕”指的是建校時間不超過50年,“大學”指的是“研究密集型大學”。本研究使用THE大學數據庫,因此簡稱研究對象為“年輕研究型大學”。
(三)分析年輕研究型大學發展的維度
有關研究型大學的概念描述,涉及本研究擬從教學、研究、社會服務的職能維度對年輕研究型大學發展狀況及模式進行分析的緣由。由于要借用THE“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數據庫資源,本研究采用其五維度分析框架,即教學(含教學聲譽、師生比、博士培養成績、師均大學收入)、研究(含研究聲譽、師均大學研究收入、師均論文數)、引用(論文引用影響力指數FWCI)、產業收入(含創新、發明和咨詢在內的來自產業和商業的校外收入)和國際視野(含國際教師比、國際學生比、國際合作論文比)。其中的“研究”和“引用”可合成為大學的研究職能,“產業收入”代表大學在履行社會服務職能上的貢獻,“國際視野”既表明擴展的大學(國際)社會服務職能,又表明新時代給大學提出的新要求。另外,因THE數據庫中采用的指標及其權重在2019—2023年間是保持不變的,故本研究采用的是2019—2023年間的數據。
(四)研究年輕研究型大學的樣本
我們并不全面掌握世界上具有不長于50年辦學歷史且發展快速的研究型大學有多少、在哪里,只能將2023年THE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TOP100作為基礎樣本池,以探索的思路開展選樣過程。
1. 關于“年輕”。一是校齡。原初設計是將21世紀建立的大學作為研究對象。但查詢發現,享有一定程度國際影響力的21世紀建立的大學很少;同時認為從僅有20多年歷史的大學發展中很難了解這個“小眾群體”的發展歷程及其趨勢。于是筆者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具有50年辦學歷史的大學。二是新建。TOP100樣本池中包括重建和重組的大學,出于我國研究的需要,本研究選擇在50年內“平地而起”的嶄新大學。經對TOP100所大學官網文獻的充分閱讀,滿足限定條件的備選大學56所。
2. 關于“快速發展”。盡管56所備選大學處在年輕研究型大學TOP100中,但需要考慮擬作為樣本的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的位置。查詢發現,56所備選樣本中有34所居世界大學TOP300位之后,分析34所大學的所有數據,發現它們的發展優勢不明顯。由于研究初衷是為了給我國新建的研究型大學尋找可借鑒的經驗,瞄準建校短時間內躋身世界大學中相對前列的大學才是本研究應當關注的對象,所以留下22所大學作為備選樣本。
3. 關于“學科”。我國新建研究型大學主要是理工多科性的,迄今為止,尚沒有單一學科的新大學呈現出如此快速發展的態勢。由于研究世界案例最終也是要為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服務,于是放棄3所2019—2022年4年數據不可得的醫學院校。
最終,以校齡不長于50年且非重建重組、居2023年THE世界大學TOP300同時居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TOP50(滿足限定的樣本自然進入)的19所多科性或綜合性大學作為本研究的樣本。其多維信息見表1。

三、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狀況
(一)總體發展描述
將19所樣本大學在5個分析維度上的得分與其計入權重后的總體得分繪制圖1。排在前兩位的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總分都超過70分,明顯高于其他樣本大學的分數:7所大學總分居60~65分之間(南方科技大學64分排在第6位),10所大學總分都在55~60分之間。

這些大學在教學、研究、引用、產業收入、國際視野5個分析維度上的表現總體上為:發展勢頭強勁的是國際視野和引用兩條折線,產業收入和研究兩條折線大致居于縱軸中段,教學基本上居圖的下半部。具體來說5個分析維度如下。
一是“引用”。“引用”得分為5所大學維度得分的最高值且邦德大學近滿分;13所大學將其各自在引用維度上的表現列為自身5個維度得分的第二名;近乎所有大學都重視論文引用;19所大學的該項均分超過83分。
二是“國際視野”。12所大學的該維度得分為各自最高分(其中8所大學得分在97分以上);但2所韓國大學的該項得分卻為自身5個維度得分中的最低值;樣本大學的該維度得分均值超過82分。
三是“產業收入”。韓國的2所大學在該維度上表現最好;香港科技大學和南方科技大學的該項得分列在各自5個維度得分的第二;19所大學的該項得分均值剛過60分。
四是“研究”。這些“研究密集型”大學的該維度表現卻呈現出“一般化”。最高分獲得者是香港科技大學,75分;最低分獲得者是沙迦大學,僅31分;19所大學的該維度得分均值不足52分。
五是“教學”。該維度所含內容的統計口徑很寬,各樣本大學的表現都不很好。14所大學在該分析維度上的得分都為本身5個維度得分的最低值,19所大學該項得分均值僅為42分。
在教學和研究兩個分析維度上,世界頂尖年輕研究型大學的得分均值竟然“不及格”,吸引我們反思THE所設計的“教學”和“研究”維度的內容合理性。如“教學”維度的內涵是否真的反映出大學教學的質量;又如將“引用”獨立設置、“研究”不含科技貢獻在內,是否真能代表對大學研究的評價。
(二)建校年代和地域分布差異
了解到樣本大學的整體發展狀況,可以再分析這些大學在不足半個世紀的發展道路上是否顯示出因校齡長短和地域不同所帶來的差異?更準確地說,校齡和地域是否影響年輕大學在教學、研究、引用、產業收入和國際視野中的表現?
1. 校齡長短與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筆者按校齡分組對樣本大學進行了研究。(見圖2)第一組是校齡不足20歲的南方科技大學和蔚山國立科技研究院,兩校在引用和產業收入上的表現都好(比較而言,南方科技大學更注重引用,蔚山國立科技研究院更注重與產業的聯系),在研究上的表現相近,在國際視野和教學兩個維度上的得分相反(南方科技大學的教學表現不夠好,蔚山國立科技研究院在國際視野上的得分較低)。第二組的校齡為21~30歲,組內4所大學的發展重點極為相似:在國際視野上的表現都極好,在引用上的表現都居各自5個維度的第二位,盧森堡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在教學、研究、產業收入三維度上的得分比較均衡,沙迦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兩維度得分都較低。第三組校齡為31~40歲,組內7所大學的發展特點互不相同,主要是在引用、產業收入和國際視野上的表現“各顯神通”。除浦項科技大學之外,6所大學的教學得分都為自身5個維度得分中的最低;浦項科技大學在國際視野上得分最低。第四組是41~50歲的“年長組”6校。6校的共同優勢在國際視野和論文引用上;阿聯酋大學和馬斯特里赫特大學的產業收入得分較高而且相近。

從圖2可以看出,論文“引用”和“國際視野”體現出強勢,除為數很少的大學外,幾乎所有校齡段的大學都很重視在這兩個維度上的表現。相反,也是除幾校之外,“教學”體現出弱勢。“研究”可被看作是“可爭取的維度”,若把“引用”納入到“研究”的范疇,目前在“研究”維度上的表現就會發生變化。最后的“產業收入”可稱為新興維度。總體來說,這些樣本大學在5個維度上的發展優劣勢并不依據校齡的階段性不同而不同。結論是,在50歲為最大校齡的限制下,大學校齡的長短與其發展維度之間并不構成某種對應關系。
2.地域分布與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已知19所樣本大學中的9所地處亞洲,7所在歐洲和3所在大洋洲。圖3可見按地域分組的樣本大學在2023年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中5個分析維度上的得分和總分。

由圖3可以看到:第一,亞洲9所大學可分在三個次級區域,含港澳地區在內的中國大學5所、韓國大學2所、阿聯酋大學2所。其中,一是中國5所大學顯示三種發展態勢:中國香港2所大學發展態勢基本相似且為世界年輕大學中的佼佼者;中國澳門2所大學的發展形態相似且特別重視“國際視野”和“引用”;南方科技大學表現獨特,其引用、產業收入、國際視野和研究、教學似四階梯順勢而下。二是韓國2所大學的共同點是強調大學與產業界的聯系,相對更重視“教學”,不太追求在“國際視野”上的表現。三是阿聯酋2所大學都重視“國際視野”和論文“引用”。第二,地處歐洲的7所樣本大學,相對而言,在“國際視野”和論文“引用”的成就很大,德國波茨坦大學在5個維度上的表現比較均衡。第三,大洋洲澳大利亞3所大學走著幾乎完全相同的發展路線:論文“引用”和“國際視野”兩維度得分極為突出,西悉尼大學和迪肯大學在五維度上的成就幾乎相同。
圖3可見,亞洲年輕研究型大學在活躍度上和發展態勢上的多樣化都高于歐洲和大洋洲的大學。特別是,9所亞洲大學中有6所在與產業界的合作關系上有了進展;中國港澳4所大學和阿聯酋2所大學在“國際視野”上的得分都很高。比較來看,亞洲大學在“產業收入”上比歐洲和大洋洲的大學做得要好,所有樣本大學在論文“引用”上的成就大致相近。細化到國家層面,由于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具有各自的社會需求程度和需求得以滿足的程度,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又直接影響到高等教育發展的階段性,如此使得年輕大學的發展特征與其在國家/地區的分布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需要提及的是,滿足共同限定條件的樣本大學中沒有得到來自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大學代表。
(三)年輕研究型大學發展的縱向變化
縱向變化指的是在本研究限定的2019—2023年內,19所樣本大學發展狀況的年度變化。首先要討論的是各校年度總分變化,再分析參與總分計算的5個維度的得分變化,想了解快速發展的年輕研究型大學是因為哪些方面的優勢進入到世界高等教育快速發展視野的。
1. 從總體上基本穩定到急劇變化的三組大學。當筆者將19所樣本大學連續5年的總分以圖4呈現時可見三種情況。第一,5年里總分保持基本穩定(變化量在5分之內)的有7所:馬斯特里赫特大學、龐培法布拉大學、奧爾堡大學、浦項科技大學、盧森堡大學、波茨坦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其中亞洲和歐洲的大學分別為2所和5所;具有30多年歷史的大學4所,2所大學剛到第50年。第二,5年總分變化不太大(在6~11分之間)的有8所:香港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蔚山國立科技研究院、提契諾大學、迪肯大學、西悉尼大學、阿聯酋大學和澳門大學。其中亞洲的大學5所、澳大利亞大學2所、歐洲大學僅1所。建校年齡分布在各校齡段。第三,總分變化很大(居15~25分之間)的有4所:南方科技大學、邦德大學、伯恩茅斯大學和沙迦大學。其中地處亞洲、歐洲和大洋洲的大學都有,所有校齡段的大學都有。這樣,樣本大學在縱向年度上,其總體的穩定或變化狀況并不以地域、也不以校齡為依據。

2. 單維度表現變化不大的年輕研究型大學。圖4的總分變化可能來自大學在某維度表現的急劇變化,也可能來自幾個維度的復合性變化。若要了解大學在辦學成就上的變化,需要對其多年成績進行縱向觀察。雷達圖能夠幫助我們形象地觀察乃至判斷這些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過程。從對19所樣本大學繪制的各校連續5年的雷達圖來看,有10所大學在5個維度上的變化都不大(馬斯特里赫特大學、浦項科技大學、龐培法布拉大學、盧森堡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提契諾大學、西悉尼大學、奧爾堡大學、迪肯大學),有的大學的某個或某幾個維度甚至基本不變。它們中有5所、3所和2所大學分別地處歐洲、亞洲和大洋洲。相對而言,歐洲的盧森堡大學和提契諾大學、亞洲的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在多個維度上的表現都有變化但變化不大。其中的盧森堡大學和澳門大學、提契諾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變化形態兩兩相似;這4所大學中的3所的校齡都居比較年輕的21~30歲之間。最為特殊的是具有38年校齡的浦項科技大學,連續5年的雷達圖均呈穩定狀態,僅在“引用”上發生變化且隨年代遞進而得分下降,在“國際視野”上的得分令人吃驚地低,但在“產業收入”上一貫表現極好。
3. 單維度表現變化很大的年輕研究型大學。大學個體在世界大學中的位置依據其總分,而總分是對大學在五維度上的得分的加權總和,所以總分依賴大學在分維度上的表現。大學都有各自的重點工作領域和著力方向,做不到也不必要做到各項工作“齊步走”。經過對19所樣本大學連續5年的五維度表現雷達圖分析,本研究發現有5所大學的縱向發展主要依賴其在某單一維度上的表現。
圖5中的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波茨坦大學的主要變化發生在“產業收入”單維度上。香港科技大學在“引用”“國際視野”“研究”“教學”四個維度上的表現基本穩定,只是2023年在“產業收入”上的得分比前一年的65分提高了30分。如此帶來該校在世界大學中的位置從2022年的第66名回升到第58名。與其相似,香港城市大學唯一的較大變化也是2023年在“產業收入”上的表現比2022年提高了30分,也使其在世界大學中的位置比2022年上升了52位,進入到前100名中。波茨坦大學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伯恩茅斯大學和邦德大學的主要變化發生在“引用”這一維度。前者從2019年的52分逐步提高到2023年的88分,后者前4年基本穩定只是在2023年得以“突進”并達到近滿分。邦德大學僅用一年時間在某一個分析維度上發生如此大的進步是難以復制的案例。
圖5呈現的是因在單維度上的大幅進步帶來的大學整體進步的實踐案例。
4. 多維度表現急劇變化的年輕研究型大學。兼顧5年縱向變化大和/或雷達圖圖形獨特的情況,4所樣本大學在多維度上的表現呈現的是急劇變化,分別是南方科技大學、蔚山國立科技研究院、阿聯酋大學和沙迦大學。
從圖6觀察到,從“蔚山科技大學”改名的蔚山國立科技研究院,在“產業收入”上的表現很好且成績連年提高(2019年70分,2023年90分);在“教學”上的得分是所有樣本大學中最高的且連年提高(2019年32分,2023年54分);在“研究”上的表現也可圈可點。盡管其在“引用”和“國際視野”兩維度上的得分連續下降,但因其在前3個維度上的進步,助力其在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中的位置從2019年的第20位提高到2023年的第10位,2023年進入世界大學的前200名(第174名)。

南方科技大學是所有樣本大學中最年輕的,從籌建日起到數據可得的2023年只是13歲,即使在年輕大學群里都堪稱一個特別的存在。5年中,其在“引用”維度上的表現居高分穩定;“研究”上的得分快速提高(2019年26分,2023年60分);在“產業收入”維度上的得分得以“過山車”式的變化(2019年不足38分,2021年達到97分,2023年回到78分)。盡管其在“國際視野”上的得分徘徊于60分前后,“教學”表現的最高分只有36分,但其在前3個維度上的成就助其在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中從2019年的第55名“飛升”到2022年的第13名,2023年進入世界大學的前200名(第166名)。從實地調研中得知,該校的國際教師和國際合作論文所占比例都很高,但其招收的來華留學生的比例不高。
阿聯酋大學的“產業收入”從2019年的47分到2023年的73分;“研究”方面從穩定了4年的30分提高到2023年的44分;“引用”上從2019年的70分到2023年的82分;“國際視野”在90分前后保持穩定;“教學”則在32分持續不動。在不同分析維度得分的正加負減使其在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中的位置從2019年的第70名上升到2023年的第38名,在世界大學中的位置相應地從連續4年的350名之后到2023年的300名之前。
沙迦大學是樣本大學中排在最后但進步最大的案例。主要改變發生在“引用”維度上的“絕對”且連年提高上(從2019年的24分逐步提高到2023年的97分);“研究”上5年提高了16分;“國際視野”保持在99分的高位穩定;“教學”方面的提高不多;“產業收入”上的提高更少。在前3個維度上的表現幫助該校在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中從2019年和2020年的第201~250名提高到2021年和2022年的第177和第89名,再到2023年的第43名,在世界大學中的位置則從2019年的800名之后提高到2023年的300名之前。這樣的進步幅度確實讓人震驚。
四、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模式
將論文“引用”固定在時鐘12點,以產業收入、國際視野、研究、教學為順時針序,用2019—2023年得分數據繪制出19所樣本大學的93幅年度狀況雷達圖(17×5+2×4)和19幅縱向發展雷達圖。在對112幅雷達圖進行對照分析的基礎上,用簡單聚類方式歸納出快速發展的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具有兩種發展模式,據其形態分別稱為“谷倉形”和“紡錘形”,本研究僅以2023年數據為代表做出圖7。

7所大學呈現出“谷倉形”的發展模式: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蔚山國立科技研究院、馬斯特里赫特大學、浦項科技大學、南方科技大學、波茨坦大學。來自亞洲的大學5所和歐洲的大學2所,處在多校齡段,其平均校齡32歲且2所20歲以下校齡的大學都在此組中。該組大學有如下特征:其一,共同的外貌形似“谷倉”,各校在5個分析維度上的表現比較均衡但也并非平均用力,也分輕重;其二,各校的“谷倉頂點”依據該校在5個維度上的表現而定:來自中國香港的2校以“國際視野”、來自韓國的2校以“產業收入”、來自中國的南方科技大學以“引用”分別為各校的“谷倉頂點”,來自歐洲兩國的2校的“谷倉頂點”互不相同;其三,“谷倉”有大小之分,香港科技大學的“谷倉”很大而波茨坦大學的“谷倉”很小。總體上看,依據2023年總分數據,排在19所世界年輕研究型樣本大學前列(前6名和第8名)的大學都呈現出“谷倉形”發展模式。
12所大學呈現出“紡錘形”大學發展模式:龐培法布拉大學、盧森堡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提契諾大學、西悉尼大學、奧爾堡大學、阿聯酋大學、伯恩茅斯大學、迪肯大學、邦德大學、沙迦大學。其中有5所歐洲的大學、4所亞洲的大學、3所大洋洲(澳大利亞)的大學,它們也都處在多校齡段,平均校齡37歲且4所接近或等于50歲的大學在此組中。該組大學具有這樣的特征:其一,共同的外貌形似“?中間粗兩頭尖”的“紡錘”,數據顯示上下兩端的“引用”和“國際視野”得分高甚至很高;其二,處在中部的“教學”“研究”“產業收入”表現比處在兩端的兩個維度上的表現要遜色許多,但各校又有各校的特色:如,阿聯酋大學的“產業收入”較有成績(得分72.5分),奧爾堡大學的“研究”不錯(得分近58分),盧森堡大學的“教學”表現亮眼(約50分);其三,“紡錘”并無明顯的大小之分,這是因為各校在5個分析維度上的表現不均衡所致。總體上看,從2019—2023年的數據呈現特點中發現,呈“紡錘形”發展模式的年輕大學在各自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特征,主要是“守住”在論文“引用”和“國際視野”兩個維度上的成就。而依2023年的總分數據,排在19所世界年輕研究型樣本大學中、后段(第7名和第9至第19名)的大學都呈現出“紡錘形”發展模式。
為了增強對前文研究得出的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呈“谷倉形”和“紡錘形”兩種發展模式的科學性,本研究采用K-means聚類方法對19所樣本大學在論文引用、產業收入、國際視野、研究、教學等5個維度上的表現進行歸類,最終得到兩組聚類中心,(見表2)分別進入此兩個類型的大學與圖7所示的呈兩種模式的大學相同。K-means法得出的聚類中心本身就清晰地表達了兩類大學之間的差異。比較來看,類型1對應著“谷倉形”,呈現這種發展模式的大學在5個分析維度上的表現相對均衡;類型2對應“紡錘形”,呈現這種發展模式的大學具有“高引用、高國際化”的特色。

本研究最終發現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模式有兩種,分別為“谷倉形”和“紡錘形”。盡管中國香港2所大學、韓國2所大學呈“谷倉形”發展模式,中國澳門2所大學、阿聯酋2所大學、澳大利亞3所大學呈“紡錘形”發展模式,盡管呈“谷倉形”發展模式的大學稍偏年輕,呈“紡錘形”發展模式的大學稍偏年長,但只能說,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模式并不具備地域分布和校齡段分布的特征。比較來看,亞洲國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相比歐洲來說更為積極主動,歐洲高等教育發展有可能處于更為成熟與飽和的狀態中。
五、研究結論和對大學排名指標的反思
中國新建研究型大學的積極性很高,在21世紀第二個25年里還會持續。本研究呈現了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狀況及其模式,我們需要博采眾長,認真學習和借鑒他國建設年輕研究型大學的經驗。本研究發現可在如下三方面回應開篇提問,并對大學排名指標進行三點反思。
(一)研究結論
1. 快速發展的年輕研究型大學不僅出現在中國,也出現在其他國家,但其發展活躍度具有國別差異,如亞洲的中國、韓國和阿聯酋、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的積極性很高,歐洲的荷蘭、西班牙、德國、盧森堡、瑞士、丹麥和英國的積極性較高。南美洲、北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積極性不高,也許是因為它們的年輕大學在THE數據庫中呈現不夠好,當用共同標準衡量時沒有大學入選。這樣看來,年輕研究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尚未在世界范圍形成競爭態勢,只是在亞洲、歐洲和大洋洲的某些國家呈現繁榮景象。這說明,新建研究型大學的積極程度與高等教育系統發展的飽和度、高等教育財政的充足度、適齡人口的峰谷變化、國際學生的流入流出等因素相關。
2. 快速發展的年輕研究型大學呈現“谷倉形”和“紡錘形”兩種發展模式。同一洲域的大學不具有相同的發展模式,但在同一國家或同一地區具有一定的共性。對于這些建校歷史短于50年的年輕研究型大學來說,若以十年為一段生命周期,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不支持居于相同生命周期的大學具有相同發展模式的判斷;也不存在建校時間越長,大學發展越好的判斷。所以,年輕大學不必擔心因年輕做不到快速進步,也無需背上歷史短不能創造辦學奇跡的包袱。校史最長的大學不一定就是某洲或某國成就最大的大學。
3. 幾乎所有的年輕研究型大學都重視論文引用和國際視野,此兩個維度同時是研究型大學的群體追求。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所樣本大學重視來自產業的收入,且它們都排在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的前列,(見圖1)這就形成一種新現象:重視來自產業的收入是大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發展的一種趨勢。韓國的2所樣本大學給我們一個新的范例,用大學與產業的良好關系彌補它們在國際化表現上的不足。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所有的樣本大學不大重視教學(指THE指標中的教學得分不高),也并不是具有教育傳統的歷史越長的大學其教學成就越高。這種對教學的重視不夠正是全球研究型大學,無論年輕還是年長,都需要盡快改變的,也給新建的研究型大學的快速成長提供了超越傳統大學的機會。
(二)對大學排名指標的反思
本研究以教學、研究、引用、產業收入和國際視野作為世界年輕研究型大學發展狀況的分析維度,這是以THE世界年輕大學排名指標為基礎的。作為研究者,需要對排名指標及其相關問題進行相應的反思。
1. 大學不能應對排名指標運行。一是指標難以表達大學發展的真實內涵。如本研究所用的“教學”維度的內涵就不能涵括大學教學的內在,“產業收入”維度的內涵也不能表明大學與產業間的關系以及大學履行社會服務職能的內在。二是指標都是量化的,必須把非量化的材料——如大學理念與精神、學風與教風等——轉換成量化數據,這種轉換產生失真,失去的可能是“大學的魂”。所以,如果應對大學排名指標運行大學,就會被不科學、非完整的指標“牽著鼻子走”,就會“失去大學的靈魂”。
2. 必須考慮排名指標背后的大學運行規律。如本研究所用的“國際視野”維度,已成為年輕大學躋身頂尖大學行列的“機會性”指標,用此作為分析維度的目的,并非為了達到幾個比重,而是要提高大學的國際知名度,擴展現代大學的辦學視野和“朋友圈”,并與他人并行在“世界前沿”;“產業收入”也如此,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得到來自產業收入的本身,在大學已走上社會、緊密連接科技的今天,其發展的生命力與大學和產業間的關系密切相關。
3. 大學的改革創新要走在指標變化的前面。從2024年起,THE世界大學排名和年輕大學排名的指標體系有了變化:“教學”維度未變;“研究”維度改變成“研究環境”維度但內涵未變;“產業收入”維度改變成“產業”維度并將“引用大學論文的國際專利數”并入內涵中,同時提高了“產業”維度的權重;“國際視野”維度中增加了“出境交換生”內容但暫未給出權重;最重要的是將以前的“引用”維度改變成“研究質量”維度,除保持用引文影響力指數(FWCI)之外,增加了“研究實力、研究優秀表現(優秀論文數)、研究影響力(被重要論文引用的數量)”。盡管THE在排名指標上的改變實屬不小,但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調整。這就需要眾多的大學實行改革與創新,用其實踐案例來豐富大學發展理論,推進世界大學發展評價上的創新。
我們已經進入社會變革的新時代,已處在由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提出挑戰的環境中,人工智能已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近乎全面的挑戰。研究型大學的重要使命“知識生產”的模式一再發生變革,大學與政府、與廣大民眾、與產業之間的關系也一再發生改變。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特別是大學,更特別是研究型大學(含年輕研究型大學),都面臨著“重新洗牌”的可能,其結果又會出現不同的大學發展狀況、不同的大學發展模式。
需要交代的是本研究存在的局限。盡管筆者堅持認為THE排名指標及其權重尚需完善,所有大學都不能按照其排名指標辦學,不能依照大學的排名目標來定位發展,但為了得到世界年輕大學的發展狀況,本研究不得不借用THE世界年輕大學的公開數據。
(感謝南方科技大學周垚和楊松楠的幫助。)
【沈紅,南方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講席教授】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5年第8期
① 凡本站注明“稿件來源:中國教育在線”的所有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稿件,版權均屬本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本網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經本站協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時必須注明“稿件來源:中國教育在線”,違者本站將依法追究責任。
② 本站注明稿件來源為其他媒體的文/圖等稿件均為轉載稿,本站轉載出于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轉載稿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在兩周內速來電或來函聯系。






 中國教育在線
中國教育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