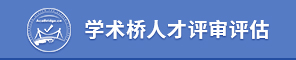有關李政道與楊振寧兩位先生的爭論,“在學術界和媒體已平靜許久。近日,一位署名為“懷疑探索者”的匿名人士在網上發了一篇《楊振寧和李政道決裂事件,有必要澄清的事實》的文章。重新讓平靜已久的這個爭論重起。盡管文章開頭,將李政道和楊振寧定位為“杰出的愛國科學家”“歷史上偉大的人物”。在結尾處也一本正經地說:“我們不必去斤斤計較科學家之間的八卦瑣事,把它們的矛盾到處擴散和宣揚,八卦這些私人恩怨對我國發展有何益處?我們要多宣傳他們的貢獻,這才是主流,是正能量。”但文章卻通篇大幅宣揚二人的矛盾,以作者的“推測”和編造來中傷李政道先生。根本不是什么“澄清”而是“攪混水”的負能量。
該文編造謬誤之處很多,一篇文章很難全面反駁。我先談談該文所說的“李政道為了反擊,和好友季承合作完成了一部《李政道傳》。季承是季羨林先生之子,季家和李政道先生的父輩就有深厚交往,可謂世交。”這顯然是毫無根據的!本人對于李政道先生和季羨林先生、季承父子三位,均十分熟悉。對他們的事情十分清楚,無需“推測”。
1963年,我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中關村分部。當時我們支部書記是季延宗(即季承),他是季羨林先生的兒子,學俄文的。那時候還不到30歲,已是中關村分部黨總支委員,負責青年和婦女工作,又是中關村分部的團總支書記,同時還兼任趙忠堯先生的秘書,可謂是少年得志,他很開明,很隨和,處理起矛盾總是很溫和。大家都挺喜歡他。那時,我作為年輕黨員常協助他組織共青團的活動。當時他很愿意學習,很用功,“文革”中還自學了英文。所以后來1979年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八七”工程時,才會派他去負責高能物理項目駐美辦事處的工作。季承是他在“文革”時改的名字。但“文革”后他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變化,與之前判若兩人。
1978年后,我與他一起參與了我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的籌備工作,1979年,我們一起認識了李政道先生。我從此時起,幾十年一直負責李政道先生到國內的接待工作并協助他處理國內事務。1983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建造后,我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不久,季承則去擔任了中國新技術開發公司總經理。此后一段時間,李政道先生與季承基本沒有來往。1990年后我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工作,同時兼管著李政道與中國科學院合作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工作。2000年我退休后,李政道先生向中央有關領導提出,希望我仍在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協助他工作。季承則在退休一段時間后,由我與另一位同仁推薦到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以顧問的名義,幫助做些文字工作。期間,曾因季承有不端行為,李政道先生曾打算辭退他,后因我與另外幾位同仁力勸才勉強留下。何來“李政道與季承二人關系匪淺,有超過30年的親密交往,友誼如同兄弟”?
李政道的父親李駿康和季承的父親季羨林根本不認識
李駿康是江蘇蘇州人,是南京金陵大學首屆農化系畢業生,畢業后在上海從事化肥生意。季羨林是山東聊城人,畢業于清華大學,1935年赴德國留學后于1946年回國到北大任教。兩人沒有過交集,李駿康與季羨林從未見過,從何認識?更何來“季家與李家的父輩就有深厚交往,可謂世交了”?
在季羨林和季承父子反目互不相見那幾年,由于我和季家父子多年的友情,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望季羨林,曾多次試圖幫助他們父子和解,未果。我曾將其父子鬧翻的事告訴了李政道先生,他好意表示愿出面請季家父子吃一頓飯,調解一下。讓我問季承,是否愿意?如愿意,則我再與季老溝通。因他與季羨林先生只在某次活動時見過面,握手、寒暄幾句而已,幾乎不認識。不宜冒然行事。季承拒絕了政道先生的好意,表示:這是家事,無需外人調解。此事也就做罷了。何來兩家有“深厚友誼”更何來世交?
李政道始終反對季承寫《李政道傳》
李政道先生認為,他如果出傳記,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多次有名作家、記者要為他寫傳,他均婉拒。同樣,也不同意季承寫李政道傳。我與一些友人也曾勸阻過季承,但他執意堅持要寫。這就與李政道先生產生了矛盾,季承2009年春被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辭退。在他離開前,李政道還明確對他說不要出版《李政道傳》。
這本書中的照片,李政道先生從未授權季承使用。季承能得到這些照片,還有一些從我與政道先生來往信件中的資料,均是因為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在2006年曾編輯出版《李政道文選》時,李政道先生給的。由于季承當時參與了該書的編輯,接觸到這些照片和資料而取得的。應該說季承是用不正當手段竊取的,是很不道德,甚至違法的。
在得知季承所寫的《李政道傳》要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時,李政道大為驚訝!于2009年3月20日致函世界出版社社長、總編,明確說明自己不同意此書出版。信中說:“最近獲悉貴社將在今年出版季承先生所寫我的傳記《李政道傳》。關于寫我的‘傳’一事,季承先生曾與我提過,可是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他何時能夠出版此書。季承先生也從來沒有為了‘傳記’事和我有明確并系統地討論過我的生平和經過。
去年我回國時看到了他所寫《李政道傳》的書稿,出我意外,忽然得知季承先生,已經和貴社簽訂了今年出版‘我’傳的合同。因為我的研究工作及學術活動十分繁忙,根本沒有時間認真閱讀。只是大略翻了一下,感到其中有不少事實不夠準確,一些說法也不夠確切。因此,我幾次告訴季先生,出版‘我’傳之事必須認真。目前不能出版,待我有時間閱改后再定。所以得悉貴社出版此書后,甚為驚訝。幾周前我又再次正式告訴季承先生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可出版此書,并請他將此意轉達貴社。
我非常感謝貴社對我的關愛,但因出‘傳’是很嚴肅的是,需十分謹慎。以前國內幾個出版社也曾多次提出出版我的‘傳記’,我均婉拒。因此,現不得不十分遺憾的正式向貴社請求,將此書出版擱置。以免造成一些以訛傳訛的不良影響。”
“世界知識出版社”為此拒絕出版后,季承又轉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因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在國內屬中國科學院代管,所以,李政道先生還給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寫信,表達對季承私自強行出版他傳記的強烈不滿,并請路院長關注。很遺憾,2010年初這本書還是在李政道先生的反對聲中出版了。
正如李政道先生所擔心的,這本不少斷章取義、拼湊及推測出來的書問世后,的確給他造成了“以訛傳訛的不良影響。”對此,李政道先生給出了一個簡潔的回答:
“季承先生出版此書(指《諾貝爾獎中華風云——李政道傳》),均系季承先生個人行動,所有問題,請直接問季承先生。”
李政道先生之所以沒有把來龍去脈公之于眾,默默地承受各種非議,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季承與父反目,正遭輿論嚴厲譴責,各方面都很困難,因而李政道認為:不能給季承這位合作過多年的同事帶來生活困難。
李政道、楊振寧兩位先生無疑是我們中華兒女的杰出代表,優秀的華夏子孫。“李楊之爭”亦無疑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幾十年來,從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開始,歷代領導人都盼望李、楊兩位先生和解。國內物理界同仁都不卷入他們的爭端,而都設法促和。我雖幾十年來負責李政道先生的接待和協助他處理些國內事務。但對楊振寧先生也十分尊敬,多次會面時,都很親切友好。口中、文中從不出不恭敬之言。期盼“懷疑探索者”及其他人不再以不負責任的“推測”來“攪混水”。
我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記述于本文的情況,就是李政道先生與季羨林先生、季承父子的關系及《諾貝爾獎中華風云——李政道傳》一書出版的實情。
(本文原標題為《我所知道的李政道與季羨林、季承父子》,作者柳懷祖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原主任、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① 凡本站注明“稿件來源:中國教育在線”的所有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稿件,版權均屬本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本網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經本站協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時必須注明“稿件來源:中國教育在線”,違者本站將依法追究責任。
② 本站注明稿件來源為其他媒體的文/圖等稿件均為轉載稿,本站轉載出于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轉載稿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在兩周內速來電或來函聯系。






 中國教育在線
中國教育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