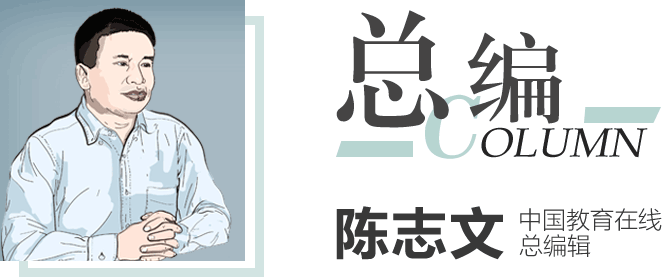最近,四川成都,迎來多所“小初高”十二年貫通式學校和“初高”六年貫通式學校。當地教育局官網相關政策解讀顯示,貫通式培養是有序推進中考改革的嘗試。成都市自2025年起,探索開展相關貫通式培養改革試點。上海市教委于10月20日發布《普通高中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將建設一批高質量完全中學和含高中階段的一貫制學校。顯然,這并非一時興起的局部創新,而是在國家“辦強辦優基礎教育”、加強普通高中建設的政策導向下,有關部門積極推進的系統性改革實驗之一。
當前,不少專家呼吁將義務教育向高中階段延伸。事實上,我國多數地區已基本具備普及高中教育的條件,特別是在新生兒數量持續下降的背景下。國家層面也明確提出將向“兩頭延伸免費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表述是“免費教育”而非“義務教育”,因為后者具有強制性。目前,向下延伸至幼兒園的免費教育已啟動具體補貼措施;而向上延伸至高中,則面臨更為復雜的局面。
這就不可避免地觸及兩個核心問題:中考以及普職分流。
2024年,我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已達92.8%,從數據上看高中教育已近普及,但問題在于:許多民眾并不將職業高中視為真正的高中。針對普職分流的爭議,有關部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建設“綜合高中”,即推遲分流節點,讓學生在高一保留普通高中學籍,至高二年級再根據個人選擇分流至普通高中或職業高中路徑。
然而,這仍有一個問題有待解決,即中考背后的高中擇校問題。誰進入由職高轉型的綜合高中?誰又能進入上海中學、學軍中學之類的名校?錄取依據是什么?部分專家,尤其是非教育領域專家在呼吁“取消中考”,但現實操作難題如何破解?難道要靠抽簽決定?
在此背景下,包括完中建設在內,一貫制學校被視為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十二年一貫制學校的實驗價值確實多元:它有利于貫通人才培養體系,特別對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發現和連續培養具有重要意義,能夠有效規避中考帶來的應試教育干擾。同時,它在理論上也能繞開或部分繞開中考這一環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長和學生的焦慮與負擔——這恐怕也是其受到許多家長歡迎的重要原因。但是,上海、成都當地教育部門都急忙澄清此舉并非取消中考。事實上,十二年一貫制學校是一個小眾試驗。
關鍵在于:取消中考就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焦慮與負擔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至少不宜過度樂觀。以中高考為代表的教育焦慮及相應負擔,本質上是社會競爭在教育階段的前置投射,其根源不在教育本身。且不論一些好的用人單位招聘時對畢業院校的嚴格設限,各地組織部門選拔選調生時,同樣明確限定畢業院校范圍。這種“出身標定”本質上是以教育評價替代人才評價,以分數門檻簡化能力判斷。
在這種情況下,家長和學生不得不在教育通道中提前展開激烈競爭,只為獲得最基本的入場券,尤其在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的當下。因此,我們需要系統性思維,不能僅表面化地看待教育焦慮。即使取消中高考,我們也無法取消社會競爭,自然也無法消除競爭帶來的焦慮與壓力,無非是其表現形式發生變化而已。如今“國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正是這種焦慮轉移的明證。
更復雜的是,這種焦慮是一個系統性難題,不會因某個環節的取消而消失。取消中考,或許能緩解中考直接帶來的壓力,但后續還有高考這一關。難道我們也要取消高考?歷史經驗表明,當年取消小升初考試后,小學生的升學壓力并未真正減輕,反而轉化為更瘋狂的校外培訓熱潮。2021年“雙減”政策出臺前,教培機構的核心客戶群正是小學高年級學生,而非中學生。這恰恰說明:競爭只會轉移,不會消失。
此外,十二年一貫制學校本身也面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入學資格如何確定?抽簽還是劃片?中間轉段機制以及如何保障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
綜上所述,我們固然應當鼓勵十二年一貫制學校的探索與實踐,但切忌過度理想化,為其賦予它無法承載的改革目標。更不能因理想化期待而扭曲實驗本身的方向。教育改革需要實事求是,在緩解當前焦慮的同時,更要直面其背后的深層矛盾——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漸進改善中尋找真正的出路。
本文首發于潮新聞